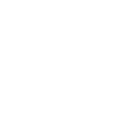黄河行(七):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河,她与我们一道经历昔日的苦难,更经历了苦难中的抗争。黄河,有数不清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走近黄河……
在沙坡头,可以骑着骆驼到腾格里沙漠里的通湖去,那是与中卫一沙相联的一个沙漠湖泊,也是紧靠中卫的一方绿洲,有林场和草原。沙坡头面临黄河拐弯的特别情景,但隔不断腾格里沙漠地下的水流与大河的水脉,腾格里沙漠里的水也好脾气,远远好过她的那些风兄弟。她知道自己不会像她的风兄弟们到处去乱闯,也就在沙漠里自得其乐,招来众多的水鸟在一起嬉戏。这样的水泡和水泊,几乎在每座大沙山之间都有,就像是天上的星星,绿洲是她们飘逸的衣衫,披着红挂着绿,在沙声、水声、林涛声乃至熙熙攘攘的市井声里起舞,天沙与地水的合奏曲在腾格里交响。
谁也不会想到,在类似通湖这样的湖泊四周,不仅有很多牧人,甚至有重要的藏传佛教庙宇。它们往往也在湖边和泉眼旁,有的湖泉甚至与著名藏族诗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紧密联系起来。那里的寺庙也有过许多次俗称“跳鬼”的宗教仪式,经幡在风中飘着,斜拖在地上的铜长号在呜呜地响着,铜铙咣咣地敲着,在热烈的驱魔攘妖场面和设定情节里,演绎着藏传佛教里特有的魔幻故事。早些年这些都没有了,至少那些不比京剧脸谱差的各色面具开始逐渐消失,喇嘛们还俗的还俗,住家的住家,留下几个无处去的老喇嘛,在冬季射着微弱阳光的寺院角落里守着。现在不同了,许多修复的寺庙比先前还要壮丽。修寺的经费大半不需要住持们托着铜钵去化缘。僧众也多起来,只要有佛学院的学习资格,就可进入,这同传统的度牒和“挂单”乃至受戒出家,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一切恢复如初,腾格里湖群边的寺声和水声依然幽远。
我非佛门弟子,因此对于逛庙还是随性和随兴的。几十年前在贺兰山林管所劳动锻炼,在贺兰山西麓的南寺设有固定的营林站,平时少不了到那里去传达一些必要的工作信息,一般是要住一宿的。闲时到这家有名的喇嘛庙去转转。记得那被称为广宗寺的南寺大得令人吃惊,从南寺沟口的台地到沟沿,大殿和僧舍海海漫漫一大片,有的是藏式建筑,有的是黄砖绿瓦的歇山式内地建筑,听说足有2000多间。最盛时拥有数千喇嘛,伙房里架设的大青铜锅就有一吨多重。人常说,天下风景僧道占半,南寺的风景深藏在山谷里,规模也不小的北寺也即福因寺,风景则显露在异石奇峡里的寺庙前。但在当时这里寺门紧闭,既看不到香客游人,更看不到披着紫衣僧装的喇嘛,只有倒在地下的经幢和大体还算齐整的琉璃瓦墙,所幸未毁成瓦砾,否则后来再恢复起来,就难了。
那广宗寺也有一个藏名,叫丹吉楞。说是早年间曾毁损于兵火,后来修复。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南寺的营林员曾带我参观了广宗寺。说那里有过一尊三寸高的镇庙之宝纯金无量寿佛金佛像,金佛像自然无由得见,但相传庙里埋着六世达赖的供奉肉身。虽说是入土为安,或者也是保护的一种方式。他原本被供奉在大经堂后的黄楼寺里。那不是寻常可见的塔院,是一个大的殿堂,两层楼阁黄绿琉璃砖瓦装饰,一共130间房,前面81间,后面49间。这里还供有相传文成公主佩戴过的宝剑。
由于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人情愫,这里具有更感人的历史色彩。他的曲折经历大家都想知晓。这里若果真是他的归宿,他的灵魂又是如何从腾格里沙漠来到这里的。他如何从藏地来,又去过哪些地方,这一连串的谜,只能从零星传闻碎片里慢慢拼接,既有偶然性,也有随机性。阿拉善的喇嘛寺院众多,似乎每个苏木甚至每个大的居民点附近都有,但最有名的有8座。其中一座就在腾格里,那里似乎是他终老的地方。
当时既无资料可查,也无从去打听,即使碰到一些曾经的喇嘛佛爷,也是浑然不知。我相识的一个叫豪比斯的青年人,曾经带我去见昔日王爷家庙的小活佛家,谈起这事,也是不甚了然。闲时想起来,只能进行一些一般的逻辑推理,仓央嘉措既然是从西藏方向进入腾格里,路线必定会是由南到北。仓央嘉措之于阿拉善的秘密线头,或许就在腾格里的一个湖里首先显露。
腾格里在蒙古语里是天的意思,如同匈奴语将天呼作祁连一样。如果仓央嘉措没有死在被政敌押进京的路上,难道他的流亡之路竟就是这条天路?那么他的第一个落脚点在哪里,他又是在哪口沙漠泉眼里掬起一捧泉水,湿润干裂的嘴唇?

腾格里沙漠风光
好在那里也有一个与我们业务有联系的林场,因此不久后,我就去到离中卫不远的沙漠盆地头道湖林场。有头道湖必有二道湖、三道湖和更多道的湖,想不到这腾格里的南缘居然有那么多的湖泊,而星星点点的林场,就分布在这些汇水盆地里。仓央嘉措的秘密也许隐藏在一座汇水盆地里。
每个林场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他们带我去看一种神秘的树,叫什么没有记住。后来有人专门考察过,似乎也没弄清这几十棵树的种属。那不是沙漠里常见的树种,大枝大干会开花。问起来历,说是建场以前早就有,当地的牧民说是“神树”,是二百多年前一位从西藏来的大活佛种下的。他们指着湖水东南边不远的一座喇嘛寺庙说,那活佛当年就住在那庙里,也圆寂在那庙里。后来,活佛圆寂后的肉身,被迎到后建的贺兰山南寺去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眼前的树,眼前的庙,不是幻觉。在同行人的陪同下,我去到了那个老寺庙,庙也不小,叫承庆寺。这里的湖是三道湖,也叫淖尔图湖,这地儿叫超格图呼热,是腾格里的一方小绿洲,离中卫城不远,后来成为阿拉善地区有名的孪井滩生态区的一部分。
这里或者就是劫后余生的仓央嘉措最后的落脚地,但他当时使用的法名,肯定不是达赖的法号。他来这里,不是孤零零一人,有12人跟随。他或者走过阿拉善的三点一线,即从最早的三道湖昭化寺和我见过的承庆寺,去过定远营。
多年之后,遍寻仓央嘉措的有关资料,也证实了我那时的部分猜测。仓央嘉措是门巴族人,在前几世达赖里,除了四世是土默特的蒙古族人,别的都是藏族人,唯有他是门巴族人。他是按照教内规则,由当时的法王“第巴”桑结嘉措寻访认定的。1697年坐床,但在1706年23岁时,就遭受了厄运。他在内部斗争中被递解,在茫茫夜色里消失了。此后,谁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关于他的结局,一直有多种版本。有说他在递解途中遇害了,有说他在五台山的藏寺终老,但最多的说法是他乘着夜色逃跑了,是有人暗中营救,还是出于本能,都是猜测。后来去了哪里,有说他去过格萨尔的故乡和更东边的峨眉山,有的说他到了尼泊尔又回来。去格萨尔的故乡和更东边的峨眉山,也许更可信些,因为那里离他的故乡门巴地区不远,而仓央嘉措本身又出生在一个红教的家庭,在红教势力范围里,可以更安全一些。那么,他最后怎么又辗转来到腾格里沙漠深处,又怎么如传说中在淖尔图湖边长留了下来呢。
仓央嘉措的遭遇,或者起于他的感情生活和诗歌创作,但那是由头,复杂的教内外派系斗争决定了他的命运。那时,进入西藏的拉藏汗与选中仓央嘉措为灵童的法王“第巴”桑结嘉措斗得死去活来,以至于“第巴”桑结嘉措给拉藏汗下了毒,自然被后者处死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仓央嘉措不被拉藏汗告御状,也会遭受别的不测。在仓央嘉措看来,“第巴”桑结嘉措是他的恩人,按照当时的规矩,法王是选定达赖灵童的第一执行人,而达赖却又是选定“第巴”转世的责任人,所谓达赖与班禅互为师徒,也有互选灵童的关系,但最后的认定权,在清朝皇帝的金瓶掣签中。仓央嘉措似乎已经认定,“第巴”桑结嘉措的转世就在腾格里方向,因此他必须到那里去寻访。
他在腾格里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一个叫朝格图呼热的地方,离他后来驻锡的承庆寺不远。那里原来有一座小庙,由朝格图老夫妇看守,因此这个地方一直以朝格图命名。后来正式建寺,一开始也叫朝格图庙,后来就承旨定名昭化寺。仓央嘉措与朝格图老夫妇谈经论法,他看中了这个地方,觉得适合建寺,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便于在这一带寻访“第巴”的转世灵童。灵童果然被他寻访到了,那就是被他悉心培养并送到藏地深造的阿旺多尔济,阿旺多尔济就是后来修建贺兰南寺并做了住持的活佛。
昭化寺的建立,无疑是他在腾格里和阿拉善重建藏传佛教王国的第一步。后来南寺落成,这里的大部僧众都到了南寺,因此这昭化寺不仅成为南寺的属寺,其实也是南寺的前身。同时也是仓央嘉措圆寂后肉身的第一个寄存地。
然而,仓央嘉措头上一抓一把的小辫子,还是传说中放荡不羁的世俗爱情。这又是怎样一股燃烧不息的爱情火焰,把他烧成那般模样,以至于拒绝了他的老师五世班禅给他授比丘戒?要知道,没有这个仪式,他永远成不了达赖。他给五世班禅重重跪下,发出毋自由宁去死的毒誓,而这场面真真确确地记载在有关五世班禅的传记里。究竟是什么,使他伤心欲绝以至于处于癫狂状态。
也有传闻,这位高僧圆寂之后,他的心传弟子在整理他的法物时,在他的胸前心窝的衣襟里,发现了一束长长的秀发,那便是传说中玛吉阿米留给他的最后纪念。这纪念似乎一直在他心窝里和他的诗歌意境里。但有没有玛吉阿米这样一位使仓央嘉措不惜抛弃荣耀地位的美丽姑娘,其实是无迹可寻的。有人说玛吉就是“未嫁娘”的意思,但一生未婚的女子多的是。也有人说,玛吉也有私生女的意思,但那又有什么呢。关于玛吉阿米,似乎有更多的传闻,有说她与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幽会,被铁棒喇嘛跟踪暗杀了,有说她被玷污后远嫁了,而那束秀发就是决绝之物。作活佛就要付出爱的自由代价,这或者是仓央嘉措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人生难题。
细读仓央嘉措的情诗,你不难看出,一个专一的诗人是如何歌唱的。这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有着燃烧不息的激情之火。尽管我们目前只能把玛吉阿米当成是仓央嘉措的爱情符号。仓央嘉措似乎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浪子,也不是不顾一切的莽撞青年,从他在腾格里许多处事的细节传说里,包括很早就开始一步步筹划新的佛教王国,就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思考周密的智者。对于仓央嘉措,我们似要有更立体的评价,不仅是他的诗,也包括他超脱的人生智慧。承庆寺是他亲自主持修建的寺庙,或者更符合他大难犹存的一种心境。他受到朝格图老人的盛情接待,或者出于淳朴的感情回报,帮助后者建立昭化寺。一个承庆,一个昭化,显现了他那时的心情。希望世俗感情能与宗教哲理统一起来,这也许是他最真实的意愿。
信仰什么很重要,但如何信仰和信仰的内容、形式同样重要。也许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水信仰”,沙漠里有水有寺就有人群,也会有生生不息的文化。
比如腾格里深处的寺庙里,常见白度母、绿度母的画像和唐卡,人们往往留足更久。不仅是因为她们汉译的名字传形又传神,形象也秀美、温馨,像是在远方念着你的大姐姐,也像是你记忆中年轻母亲的某种神态。也是因为她们在本经里,有着一种对人生的最终关怀,是草原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文成公主和那位尼泊尔公主,也曾被奉为白度母、绿度母的人世化身。在白度母绿度母的咒语里,没有过多的说教和暗示,只要心气合一地念,心里也就平和了许多。或许那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治疗,但哪一种病痛和哀伤又同自我心理过程变化没有关系呢。
我更喜欢听喇嘛们用男低音念诵的“白度母咒”和“绿度母咒”,舒畅的共鸣和有韵律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心灵慰藉。据说,现在梵呗音乐也开始流行了,有一位叫桑吉平措的青年歌者,被称为“天籁王子”。我还没有机会在现场听过,但我相信那不会是乱捧。男高音女高音固然好,但宏厚的低音更显珍贵稀少。后来也听过一位年轻的喇嘛念过“白度母咒”,那美的男低音,真有些出自天籁的感觉。
佛教,无论是藏传还是汉传,都有世俗的一面,否则就少了信众与“粉丝”。有的时候,正常的世俗气,会让你找到浸淫在生活原态的感觉。一次我到阿拉善的北部去,在与巴彦淖尔交集的地区有座阿贵庙,居然是藏传佛教中比较古老的红教,以莲花生大师为本尊。阿贵,山洞也,不会有大的风景,但它让我想起在西藏林芝南山曾经看到过的一所红教寺庙。那里的喇嘛是住家喇嘛,活佛也是坐家的活佛。主殿是一座木的佛塔,佛龛里有许多莲花生的塑像,也有酥油灯盏,但没那么多,一圈既俗也僧的人席地而坐,个个都像“自在佛”,而通向庙门的台阶上则是两个显眼的生殖图腾柱,大大方方地立在那里,浑不似密宗欢喜佛那么隐秘,那是一种原始自然宗教的遗留。因此,看到红教寺庙,有时也会突然想起从红教地区走出来的仓央嘉措,他的表现为什么会有那么不寻常。

工人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种植花棒
然而,我更多的心思在腾格里的泉和湖。我想过,那里的湖水泉水也许会与地面上的河流暗通,虽然肉眼找不到其中明显的联结线,厚厚的沙丘又阻挡着水气和云气。但有道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那沙漠不过是自然给大地披上的被子,穿透这层厚被,焉不知,它们彼此的水灵气会怎样接近。在腾格里的朝格图呼热,我就见过一眼水冒二尺的喷泉,哗哗地流淌到淖尔图湖即三道湖里。临近中卫市区的通湖名字叫得好。通湖,通湖,不管通向哪里,怎么一个通法,它们的气息终究是与大江大河相通的。
在中卫沙坡头的几天里,也曾骑着骆驼到这个通湖。在驼背上摇晃,眼望着无风时柔软的沙和沙丘下的草,蓦然忆起,多年前在塔里木轮南油田里见到的一个“实验小温室”,也想起新近传播的一则新闻。那“小温室”里红红的番茄,就是用沙漠里的地下水浇灌的,果实小些,但红得可爱。员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底下有的是水,只是矿化度高些,处理一下,完全可以种植蔬菜。听到的新闻里则说,塔里木沙漠之下是个地下海洋,至少有几百亿吨水。腾格里的下面,会不会也是一样,从攀上高沙丘的骆驼骑峰上瞭望,不远处闪着银光的便是湖盆和水线。再回头望望来路上的沙坡头,那分明就是“腾格里海”与黄河之间的一道大沙坝,坝里坝外看似两重天,但坝里坝外又是同一片大地,同一条水脉,黄河在腾格里的边上。已经流出了新传奇,还有什么更传奇的场景出现?
在东边的方格草障和一排排杨树间,一列火车从胜金关的隧道里驶了出来。胜金关,以前不知道它为何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名字,现在似乎有些懂了。胜金就是胜过金子。沙坡头的方格草障聚的是金,沙坡头大桥下的黄河也在流金淌银,腾格里沙漠在沙坡头驻足,“万斛堆”前有金玉。西北风沙千古事,居然在胜金关前开始安静下来。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王星)
凡本网注明“来源:企业观察网”的所有作品,均为《企业观察报》社有限责任公司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企业观察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企业观察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法律责任。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相关作品刊发之日起30日内进行。联系方式:010-68719660。